发布日期:2023-09-23 作者: 小九体育直播app
田余庆先生作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范畴的大师,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可谓中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紧密的推理、详尽的考证以及生动凝练的言语,给笔者留下了深入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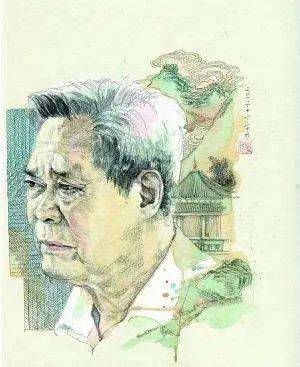
东晋江左几个侨姓大士族的沉浮兴衰,是全书调查的主线。晋元帝与琅邪王氏宗族协作,创始了江左的东晋朝廷。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宗族的各位头面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先后与司马氏共享政权。
门阀与皇权“共全国”,是东晋最基本的政治特征。按田余庆先生的归纳,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散御边。
全书以“王与马,共全国”一句谚谣的考辨发端,提醒了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和琅邪王衍的结合,与东晋初琅邪王司马睿和琅邪王导的结合的根由。虽然二者都是“王与马”的结合,但从前者到后者,政权的主导权已从司马氏搬运到了琅琊王氏。
在东晋立国之初,虽然皇权几经挣扎,从晋元帝假手于刘隗、刁协,到晋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企图冲击门阀实力、重振皇权,但终是没办法脱节“号令威权多出于强臣”的局势;
到东晋后期,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相继凋谢,几大宗族里再没再次呈现可以独立自主的头面人物人物,这本是重振皇权的大好机会,偏偏当权的孝武帝和胞弟司马道子是对“昏君乱臣”,使得皇权重振的或许“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①。

“士族擅权”的门槛是“士族专兵”,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军权与要藩的每次抢夺、转手。
士族代表人物相机而动的审慎抑制、欲取先予的远见卓识,以及“荆扬之争”的地舆政治学,都得到了浓墨重彩与详尽入微的论述。深思远虑的郗鉴、足智多谋的桓温、知难而退的谢安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入的形象。

全书很大篇幅用于调查流散装备。仅凭文明士族并不足以支撑政权。而在侨姓士族主导的江左政权中,吴姓士族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办法跻身于控制阶级上层,故而在既得的经济利益上也毅然不会退让,他们绝不能忍受朝廷征发田户、客者等藏匿人口为兵。这又使得朝廷的兵役征发越发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南来、止于江淮的流散群成为了东晋朝廷注视的目标。江左朝廷吸纳这种力气,令他们承当江北防务,用做抵挡少量族南侵的军事屏障。如京口重镇的北府兵和襄阳重镇之兵,皆以流散装备力气为根底。
在这种情况下,流散装备成为影响东晋政局不可或缺的首要的要素。王敦之乱的平定,有赖于郗鉴等人在朝廷与流散群之间的联络;郗鉴的上位,其背面依托的是他在京口军事力气的存在;苏峻之乱则是流散装备对朝廷甚至门阀政治的反噬。

总归,皇帝垂拱、士族擅权、流散御边,此三点是东晋门阀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门阀政治的重要支柱。但跟着时刻的消逝,门阀政治的这三大支柱,也在慢慢地被冰解。
与先秦的贵族政治不同,因为秦汉时期集权帝制强壮的前史惯性,东晋的皇帝一直“心底珍藏着秦汉大帝国的前史回忆,若有或许,他们就将再度蔓延君权,再现秦皇汉武的无上威严。”② 皇权与门阀的权利争斗或明或暗,一直未停过。
这一现象在淝水战后愈加公开化,先是在前秦戎行渡淮后如此危急关头,孝武帝启用同母弟司马道子为录尚书六条事,与谢安共录尚书事,切割谢安的权利,再到战后谢安未有封赏。孝武帝依托司马道子,完成了“今住上亲览万机,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大大加强了皇权。
但偏偏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皆荒淫无度,有甚于门阀士族,使得蔓延和康复皇权的重担终究落在了刘裕身上。
田余庆先生指出,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保持其政治控制又有必要事功武力。士族名士“放浪形骸之外”者简单获得盛名,但处高位以保证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长于运营武力的名士。
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不断有这种人呈现,门阀政治的连续实际上靠这类人保持。但通过三四代之后,士族迂腐程度遍及添加,且士族往往又是在几大士族之间的极小范围内通婚,不可避免地呈现生理学上的人才退化趋势,使得士族内部可以善事功运营武力的的人才越来越匮乏,越来越无力擅权。
以最典型的流散装备北府兵为例,从郗鉴到谢安,无论是用于内部奋斗仍是用于外战,北府兵一直是一支门阀士族兵,指挥权在门阀士族而不在流散帅。
但随着后期门阀士族再也没能呈现善事功运营武力的人物,连着指挥权也一起丧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流散帅和他的戎行在军事上开端获得独立性,但他们的政治方向仍不清晰。
以刘牢之为例,他虽握有一支决议建康命运的戎行,却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而走上死路。田先生为其表明怅惘,“他一直是为了自存,而又总算无法自存”③。
一起,田余庆先生还指出刘牢之的一叛再叛,并不仅仅个人进退失宜的问题,更是原本作为门阀士族的东西的武将转化为社会控制力气时必定呈现的弯曲。他没有也很难有推倒门阀政治的自觉,只能以自己的失利,为刘裕开辟路途。

概言之,跟着时刻消逝,门阀政治在跳过其高峰之后,其所依靠的皇帝垂拱、士族擅权、流散御边都在不同程度上分裂。当司马氏不能照常垂拱而居,而士族亦没有满足的力气保持政局时,现已走到前史前台的流散帅,必将反噬本来将其视为控制东西的门阀政治。
所以,在田余庆先生看来,东晋的门阀政治,仅仅“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呈现的皇权政治的反常。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渐地回归于皇权政治”。
在全书收束之处,田先生又提出:“从微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悉数前史运动的整体,其干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个结论,被阎步克先生归纳为“北朝干流论。
那么北朝何故能成为南北朝的政治干流,成为通向隋唐帝国的前史出口呢?田余庆先生指出,南朝皇权重振的动力来自次等贵族,而北朝重振皇权的动力来自军功贵族。
阎步克先生弥补了一点,江左次等贵族重振皇权的动力和力气,远不如北朝的军功贵族大。所以,虽较之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的皇权已有所复兴,但士族政治根深蒂固,士族实力“衰而不僵”,与次等士族缠腿绊脚,没能构成一个新式的政治力气,然后走入了前史的死角。
而北朝的皇权则是真实具有独裁威望的,强壮的皇权加快了官僚准则的复兴,终究使得北朝成为完毕那个年代的前史出口。

魏晋玄学家们崇尚清谈,他们抱负的君主,“不是汲汲于法令刑名的法治式帝王,也不是汲汲于礼乐教化的礼治式帝王,而是清静无为、心在山林的道家式君主。”④
但是当他们所神往的垂拱的皇帝真实呈现了,实际的政治并没再次呈现所谓上古圣王的“垂拱而全国治”,反而是门阀士族的相互排挤,政治奋斗纷繁复杂;北敌寇边,时有偏安不保之势;内部农民起义,公民抵挡。如此,笔者不由感叹,垂拱亦未必全国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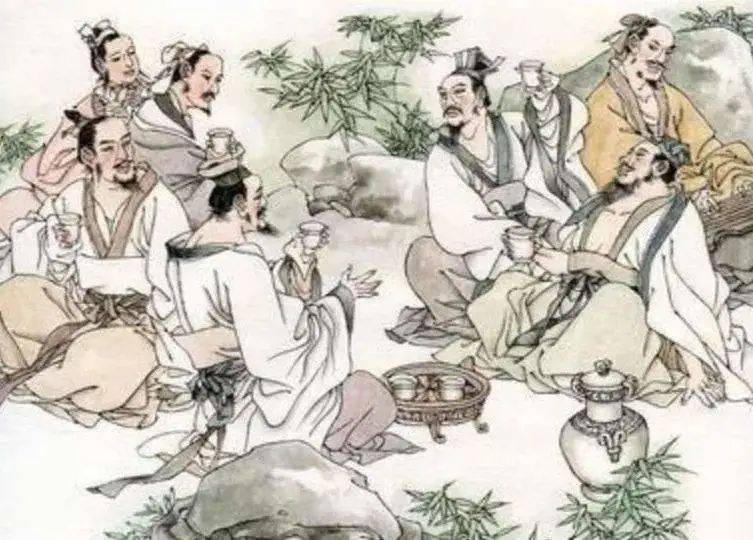
①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59 .
③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73 .